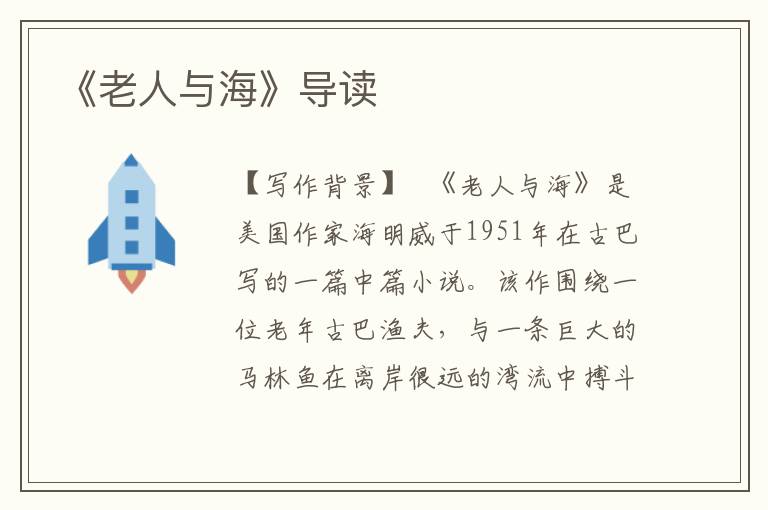《乡土中国》的社会本色
《〈乡土中国〉的理论结构》一文,把《乡土中国》全书14篇分为六章,进而将其归纳为三个理论层次。下面分别论述三部分的理论内容。先剖析各篇的论述层次,再揭示各篇的要义及关系。
一、《乡土本色》的理论要义
《乡土本色》不仅是第一章的核心,也是全书奠基性篇章。要把握乡土中国的“社会本色”,必须先读透《乡土本色》;要读懂《乡土中国》全书,也必须先读透《乡土本色》。理论著作是概念、范畴、命题的体系。只有解剖了论著的论述结构,才能把握论著的理论精髓。因此,要读透《乡土本色》和《乡土中国》,就应当超越表层的自然段落,把握深层的逻辑层次。为此,本文围绕文章中心,梳理内在理路,分出逻辑层次,拟出小标题,力求把散文化的论述,转化为学术性的论述。
(一)《乡土本色》的论述思路
“乡土本色”,即“乡土中国的社会本色”,围绕这一中心,作者对乡土中国的特点作了多层次的论述;而从人和人的关系看,面对面的“熟人社会”,是乡土中国的本质所在,也是全文的歸结点。全篇17段,从内在论述思路看,可分6个逻辑层次。
1.“从基层上看去,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1段)。
“基层”一词尤为重要,它对全文及全书的研究对象,做了明确而又严格的规定。这一段的重要性,下文再谈。第2段到第15段,从四个方面阐述了“乡土中国”的四大特点。
2.乡土中国是“种地谋生”的农业社会(2—3段)。
乡土中国离不开“土”,乡下人的谋生方式是“下田讨生活”。因此,乡土中国是靠“种地谋生”的农业社会,形成了“土是命根”的传统。
3.乡土中国是“不流动”的定居社会(4—6段)。
“不流动”是由“种地谋生”的生存方式所决定。农业与游牧或工业不同,它直接取资于土地。土地是“搬不动”的,庄稼是无法“行动”的,伺候庄稼的人也不能随意“流动”。因此,安土重迁的乡土中国,成为一个“不流动”的定居社会。
4.乡土中国是“聚村而居”的村落社区(7—10段)。
“聚村而居”是乡土中国的社区特点,与“不流动”的定居性,有联系又有区别:“不流动”是从人和空间的关系上说的;“聚村而居”则是从人和人在空间排列关系上说的。“聚村而居”的中国农村,不同于“单门独户”的美国农村。
5.乡土中国是礼俗性的“熟人社会”(11—15段)。
“熟人社会”又是聚村而居的“地方性”的直接结果。“乡土社会在地方性的限制下成了生于斯、死于斯的社会。”每个人都是相互熟悉的。于是,聚村而居的社区,成了没有陌生人的“熟人社会”。在熟人社会中,人们可以在规矩的熟悉中获得自由和信任。
6.乡土中国进入现代社会的流弊(16—17段)。
乡土中国的“熟人社会”是温情和诗意的。但有两个流弊:一是认知上是个别的,不追求普遍原则;二是熟人社会养成的生活方式,不适应陌生人组成的现代社会。这是全文的总结,也为后文论述乡土中国向现代社会的变迁,留下了伏笔。
全文六个层次,除开头和结尾,中间四部分,“种地谋生”“不流动”“聚村而居”“熟人社会”,呈现出互为因果的内在联系。
(二)《乡土本色》的理论要点
“乡土社会”的规定和“熟人社会”的提出,是本篇的两大要点,它对读懂全书极为重要。
1.《乡土中国》研究的是“基层”的乡土社会。
本文开篇说:“从基层上看去,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重刊序言》又说:《乡土中国》尝试回答的是“作为中国基层社会的乡土社会究竟是个什么样的社会”。作者反复强调“从基层上看”“中国基层社会”,这是对研究对象所作的规定。换言之,“乡土中国”是全书的研究对象,但这只是“从基层上看去”,就“基层”而言,才能说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它不是指从基层到上层的整个中国社会。
任何一个社会都可以粗分为三个层次,即基层的乡村,中层的城市,上层的国家政治。中国社会同样是复杂多样的:一方面,“从这基层上曾长出一层比较上和乡土基层不完全相同的社会”;另一方面,“在近百年来更在东西方接触边缘上发生了一种很特殊的社会”。但是,这些“非基层”社会的特性,都不在本文和本书的讨论范围之内。本书的讨论范围,严格限定于“基层”的“乡土中国”。这样的“乡土中国”,用社会人类学的语言来描述,就是“小型的、孤立的、自给自足、各自抱团的群体”6,也不妨用“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凿井而饮,聚村而居”来形容。理论是对象的客观延伸物;离开了特定的对象,真理就可能变成谬误。因此,阅读本书,把握住“基层”的“乡土中国”这个对象,至关重要。
“乡土中国”不只是本文和本书的对象,也是费孝通终生关注的对象。可以说,“乡土中国”是费孝通的研究对象,“乡土重建”是费孝通的学术志向,而“志在富民”则是费孝通的终生理想118。“基层”的“乡土中国”,对于费孝通具有多重意义。
2.“熟人社会”是乡土中国的社会本色。
从基层上看去,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而乡土中国的本色或本质,则是一个面对面的“熟人社会”。“熟人社会”是《乡土本色》的核心概念,也是乡土中国的本色和本质。
首先,“熟人社会”是《乡土本色》的核心概念。《乡土本色》共17段,2至15段谈论“乡土中国”的特点。“乡土中国”与“熟人社会”,一体两面。因此,换一个角度,乡土中国的特点,就是熟人社会的特点:乡土中国是种地谋生的农业社会,这是熟人社会的生成根基;乡土中国是不流动的定居社会,这是熟人社会的空间格局;乡土中国是聚村而居的村落社区,这是熟人社会的社区特点;乡土中国从熟悉得到自由和信任,这是熟人社会的行为规矩;乡土中国人的认识是个别的,不追求普遍原则,这是熟人社会的认知特点。
其次,“熟人社会”是第一章的核心概念。第一章包含《乡土本色》《文字下乡》《再论文字下乡》三篇;其中,《乡土本色》是核心,《文字下乡》和《再论文字下乡》是延伸性或派生性的。二者是一种因果关系:乡土中国是聚村而居的“熟人社会”,而不是现代的“陌生人社会”;既然乡土中国是“熟人社会”,是“面对面的社群”,因而也就无需间接传情达意的文字媒介,而成为“无文字社会”了。
作者在《文字下乡》中说:“在熟人中,我们话也少了,我们‘眉目传情’,我们‘指石相证’,我们抛开了比较间接的象征原料,而求更直接的会意了。所以在乡土社会中,不但文字是多余的,连语言都并不是傳达情意的唯一象征体系。”总之,只有“熟人社会”,才可能是“无文字社会”。《文字下乡》和《再论文字下乡》关于“文字多余”的论述,是由“熟人社会”派生的,也是就“熟人社会”这个特定对象而言的。
再次,“熟人社会”又是全书的基础性概念。《乡土中国》的学术任务,是尝试回答一个问题,即“作为中国基层社会的乡土社会究竟是个什么样的社会”?而“乡土社会”的本色就是“熟人社会”。因此,第二部分二至五章谈论的四大问题,即差序结构、家族制度、礼治秩序、长老统治等等,就是对作为乡土本色的“熟人社会”的多角度阐释。阅读《乡土中国》,应当围绕“熟人社会”来理解上述问题。
二、“文字下乡”的论述思路
文字是怎么产生的?作者指出:“文字的发生是在人和人传情达意的过程中受到了空间和时间的阻隔的情境里。”在面对面的熟人社会里,人和人传情达意可以不受空间和时间的阻隔。因此,乡土中国成为“没有‘文字’的社会”。这是“文字下乡”两篇文章的基本观点。围绕这一观点,作者从两个角度论述,《文字下乡》谈“无空间阻隔”,《再论文字下乡》谈“无时间阻隔”。
(一)《文字下乡》的论述思路
《文字下乡》着眼于“空间阻隔”,在面对面的乡土中国,传情达意没有空间阻隔,因此文字是多余的。《文字下乡》是一篇驳论文字,从内在思路看,19个段落可分5个层次。
1.乡下人多“文盲”,能说乡下人“愚”吗?(1—5段)
首先以理反驳,乡下人在城里人眼里的“愚”,是知识问题而不是智力问题;识字是知识问题,识字不识字并非判断愚不愚的标准。再以事例反驳,“教授孩子”和“下乡孩子”智力相等,各有不同的能力。
2.乡下人不识字,因为面对面的熟人社会无需文字(6—8段)。
作者提出正面观点,乡土社会的人在熟人里长大,是“面对面的社群”,人和人的接触不会发生阻隔;因此,文字是“多余”的。
3.文字传情达意是不完全的,作为间接传达工具是有缺陷的(9—12段)。
从文字的媒介特性,进一步说明面对面社群文字的多余:文字作为间接传达工具,易受时空影响,要讲究文法和艺术减少“走样”;文字是间接的说话,是不太完善的工具,在直接的接触中,有比较完善的语言。
4.在面对面社群里,语言并非传情达意的唯一手段(13—18段)。
再进一步,在面对面社群里,语言也并非传情达意的唯一手段:语言是用声音来表达的公共象征体系,语言只能在具有相同经验的社群中使用;而在一个社群里,除共同语言之外,还有少数人组成的“亲密社群”中的“特殊语言”;“特殊语言”的有效性,在于它可以摆脱字句的固定意义,产生“无言胜似有言”的效果。所以,在面对面的乡土社会中,不但文字是多余的,连语言都不是传达情意的唯一象征体系。
5.乡土社会多“文盲”,是由于乡土社会的本质决定的(19段)。
重申和总结全文。作者不反对文字下乡,而是提醒提倡文字下乡的人,应当充分认识乡土中国的社会本质;乡土社会多“文盲”,并非出于乡下人的“愚”,而是由熟人社会的本质决定的。
本文说理和事例相结合,说理层层推进,事例顺手拈来。文中的事例,都应视为社会学家“实地调查”中获得的具有社会学意义的案例。《乡土中国》中的事例,都应作如斯观。
(二)《再论文字下乡》的论述思路
《再论文字下乡》着眼于“时间阻隔”,在生活方式反复定型的乡土社会,人们靠语言传递世代经验,因此文字也是多余的。全文16段,包括过渡性的开头和最后的总结,可分7个层次。
1.本篇的角度和思路(1—2段)。
这是过渡性层次,交代论述的角度和思路。文字具有打破时空阻隔的双重功能。前一篇谈空间阻隔,即面对面的乡土社会不必求助于文字;这一篇谈时间阻隔,即乡土社会的经验和文化传递,为何没有时间阻隔,为何可以无文字传递。时间阻隔有两个方面,即个人的今昔之隔和社会的世代之隔。
2.打破个人的今昔之隔:感知记忆与词(3—4段)。
我们的生活经历了“从定型到不定型的过程”;换言之,作者把社会分成“不定型社会”和“定型社会”两种。先从不定型的现代社会说起。在这种情形中,人是靠词和记忆同时间接触的,也就是靠感知记忆和词即概念,打破个人的今昔之隔。
3.打破社会的世代之隔:文化记忆与词(5段)。
同样,在不定型的社会,人又是靠文化记忆和词即概念,打破社会的世代之隔。“我们不但要在个人的今昔之间筑通桥梁,而且在社会的世代之间也得筑通桥梁,不然就没有了文化,也没有了我们现在所能享受的生活。”
4.一切文化中不能没有“词”,但不一定要有“文字”(6-7段)。
词是人和时间关联的主要桥梁,但是词却不一定要文。文是用眼睛看得见的符号,就是字。词也可以用声音发出来的符号,即语言。因此,一切文化中不能没有“词”,但不一定要有“文字”。
5.乡土中国是生活方式反复重演的定型社会(8—11段)。
人和时间的接触靠记忆和词。人在记忆上的发展程度是依据生活需要决定的。乡土社会是安定的,历世不移的,是同一方式的反复重演的定型社会。个别的经验就等于世代的经验;经验无需不断累积,只需老是保存。
6.定型的乡土中国,语言足够传递世代经验(12—15段)。
乡土社会的定型生活,记忆成为多余。它不同于不定型的都市生活,不需要文字,也不需要历史。在这种社会里,语言足够传递世代经验了。简言之,定型的乡土社会是通过“语言”来打破个人的今昔之隔和社会的世代之隔的。因此,从时间阻隔,乡土社会同样是一个无文字社会。
7.中国是乡土社会,怎么会有文字?(16段)。
从时间阻隔看,乡土社会同样是一个无文字社会。那么,“中国如果是乡土社会,怎么会有文字呢?”从历史看,中国的文字不是在基层上发生,最早的文字是庙堂性的;从现实看,中国社会乡土性的基础发生了变化,文字才能下乡。这一段是全文的总结,也对两篇“文字下乡”要义作了概括。
三、如何理解对“文字下乡”的质疑?
《乡土中国》出版后受到高度关注,肯定其理论贡献,也不乏质疑之声。对两篇“文字下乡”的观点,批评者曾从不同角度提出质疑。
首先,联系生活实际,端木蕻良就曾疑窦丛生。他在《评费孝通〈乡土中国〉》一文说:“费先生肯定的说乡下人并不愚,我很同情,一个乡下人并不比一个大学教授糊涂,这是实情。但是说乡下人因为能当面说话,不需要文字,甚至还认为文字是‘走样’,这都是扯淡。乡下人要唱本看,要唱本听。他们要记豆腐账,要写状子,要看明白官府的告示,他们也要写信。他们强烈的要求生活和满足生活的传达工具并不比城市人差。”这不能說没道理。
其次,联系中国教育史,也不免提出疑问。从西周到春秋,中国逐渐形成由“国学”“乡学”和“私学”构成的教育体制。《礼记·学记》记载,西周的乡学是“家有塾,党有庠,遂有序”。从家开始,即有“家塾”教育。同时,中国人高度重视“儿童教育”。《周易·蒙卦》“彖辞”有句名言:“蒙以养正圣功也。”由此形成了乡村蒙学教育的传统。春秋时代,孔子成为私学教育第一人,提出“有教无类”原则。“耕读传家久,诗书继世长”,成为中国人的传统;“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成为乡村读书人的理想。
再次,“乡土中国”的界定,似乎也有欠严谨。有学者认为:“费的根据出自一个小时空,而《乡土中国》意在概括一个大时空的特征……;作者未设定时限,就是说他要概括漫长历史中延续、积淀成的乡土社会特征。不幸,上世纪三十年代江村那个小时空中文字与教育的衰落,未必反映大时空的特征。”“乡土中国”的学术界定,至少应包含三个方面,即时间、空间和内容。费孝通强调的“基层”是空间位置的界定,但未设定时限,也未设定生活内容。乡土中国的生活,除了面对面的日常传情达意,还有端木蕻良所说的经济生活、政治生活和文化生活等等,这显然离不开文字。
如此种种,费孝通一无所知吗?当然不是。一方面,费孝通的研究方法不同于历史学家钱穆:“他是从历史上的事实出发,我是从看得见的现实出发”288;另一方面,两篇“文字下乡”具有学术性和时评性双重品格,包含了对“平民教育”工作者某些不切实际的认识和做法的批评。1948年8月,晏阳初发表了《开发民力建设乡村》一文,认为“建乡须先建民”,主张通过教育来开发农民的四种“力”以建设乡村,即“知识力、生产力、健康力、组织力”397—401。费孝通随即发表了《评晏阳初〈开发民力建设乡村〉》的文章,对晏阳初的主张提出了批评。此文可视为“三论文字下乡”。
首先,晏阳初这是以“传教精神”了解教育:“所谓传教精神就是先假定了自己‘是’去‘教育’别人的‘不是’。传教就是‘以正克邪’……晏先生认定了‘愚贪弱私’的罪恶,然后可以着手‘教育’;以知识去愚,以生产去贪,以卫生去弱,以组织去私。”费孝通从实地观察出发,“不能同意”中国农民到现在还没有“自觉”的看法,认为应当承认每个人都有他的判断能力和理性;“教育并不是以‘有’给‘无’,更不是以‘正’克‘邪’,而是建立一个能发展个性的环境”。
其次,晏阳初“对中国农村问题的诊断缺乏真正的信念”,把复杂问题简单化,“把中国问题看成是单纯教育问题”,单纯看成“靠文字下乡”“以知识去愚”的问题。无视社会矛盾症结所在,高唱“以知识去愚,以生产去贫,以卫生去弱,以组织去私”,实效难料。
进而,费孝通问道:在生活的“苦难”中,在“这套现实的教训中,他们还会不觉悟么?还得靠识几个字才能知道他们自救的道路么?——我这样说并不是否定晏先生的千字课的价值,更不是否定文字下乡。而是说,农民并不是从千字课中得到自觉,而是自觉之后才需要识字,才喜欢晏先生的千字课。这个分别很重要,因为农民已经自觉的不单纯要识几个字,他们还要靠自己来纠正这不合理的社会结构”503—511。
换言之,如果说传统乡土中国是面对面的熟人社会,所以“文字是多余的”;那么在当年的旧中国,在“乡土重建”的现代,只有先纠正和改变“社会结构”,自觉的农民有了新的需要,“文字才能下乡”。这是费孝通谈“文字下乡”的深意之所在,也是文化功能论的基本观点,纯学术的种种质疑也可以涣然冰释。
微信扫码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