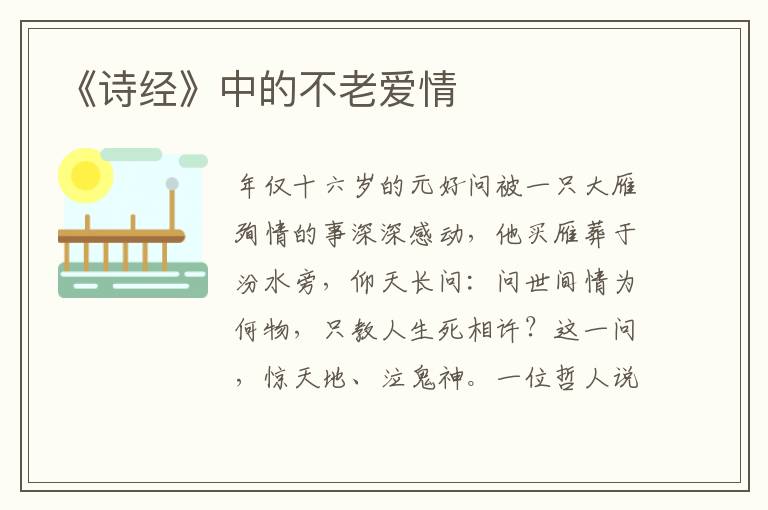死亡与爱情 ——《古诗十九首》
公元2世纪中后期——具体一些说,汉桓帝、灵帝时代,是一个让他们摇头不迭、感慨万端的时期。东汉开国之君光武帝开始剥夺相权而集于皇帝一身,其结果恰恰造成东汉绵延十几代的皇权旁落。野心家一茬又一茬,小人成群结队,而君子则血流成河。
桓帝延熹九年(166),第一次党锢之祸;灵帝建宁二年(169),第二次党锢之祸。这两次党锢之祸几乎把正直官吏和太学生罗织殆尽,把国家的生气扑灭殆尽,知识分子终于认识到汉统治已不可救药,并最终弃它而去。这种抛弃是双向的:走在末路上的汉朝廷也不再需要知识分子。
《古诗十九首》的作者即是这种社会与政治的“多余人”,既已被现行政治体制排除在外,绝望于生命的对象化,他们便开始关注生命自身。他们高唱“何不策高足,先踞要路津”,但他们自己都知道,这只是空谈。他们虽不放弃“先踞要路津”的希望,在冷酷的现实面前,他们还是冷静而安分守己的。所以,我们在《古诗十九首》中看不到真正的政治热情,看不到河清海晏的政治理想,也看不到负责任的政治讽谏。面对权势者的朱门酒肉与五马翠盖,他们甚至都少有愤怒,只是远远地一边艳羡,一边认命地叹息。他们所写的,是逐臣弃妻,朋友阔绝,游子他乡,死生新故,偏偏不谈政治。他们不言志,不载道,只缘情。
社会已经无道,他们已经无志。当知识阶层激越的清议之声被朝廷的诛杀之声压制下去之后,政治已不再是他们实现理想个人与理想社会的手段,而是权势者们压迫人民、杀戮异己的工具。这个时候,他们只能背对朝廷,甚至远离大都市,在孤馆春寒或深窗秋怨中默默消磨他们的生命与热情。一边消磨,一边枉自嗟呀,自怜自爱,承受着物质上的穷乏与精神上的不平衡,体验着个体生命被抛向孤独一隅的失意与痛苦。
这是一个没有热情的时代,没有理想的时代,没有目标没有方向的时代。历史的马车在一个气息奄奄、朝不虑夕的朝廷的有气无力的鞭影下向着夕阳走下坡去。在这种没落的气氛中,即使他们想有所作为,也是“可怜无补费精神”。于是,他们的思虑自然是沉下去,沉下去,越沉越深,越来越收缩,最后便只凝于深深的一点,只有这一点才是那麻木不仁的时代中唯一真实可触的感觉——那就是个体生命对这个寂寞而寒冷的世界的独特体验。这世界对他们漠然无视,他们对这个世界也就无所关心,他们只能关心自己的生命,并由惊讶于自己的一头风霜而惊心于生命的流逝,而后又由慨叹自己的苦难生涯而猛醒这一切的不值,“及时行乐”的思想油然而生。
死与爱,是文学中最有魅力的两大主题。《古诗十九首》的作者们,在惊心动魄地描写死亡的同时,又勾魂摄魄地写出了情爱,写出了爱的忠贞与恐惧,爱的弱小与强大,爱的专一与易变,爱的难得与巧遇。爱,就是爱的能力,是爱人的能力,是承受爱的能力。古诗的作者们在痛感自己的虚弱、痛感自己面对“世界”的无力时,发现自己竟然还有爱的能力!这是人性死灰中的余烬,是古墓中的谷种,是冬日的残荷,是夏日的最后一朵玫瑰;还像是走夜路而胆怯的人的口哨。这是颤抖的爱,惧怕的爱。《涉江采芙蓉》《行行重行行》《冉冉孤生竹》……十九首中,竟有十一首直接写到了爱与爱的牵挂!这一丝牵挂,是他们留在这世界的唯一理由,是他们生命的唯一价值,是世界给予他们苦难生命历程与愁苦心灵的唯一安慰和报偿。于是,他们把爱写得百般温存,万种柔情,令人恻然心伤而又温馨无比。他们几乎使我们相信,他们是那个时代的最后体温!
冉冉孤生竹,结根泰山阿。与君为新婚,兔丝附女萝。
兔丝生有时,夫妇会有宜。千里远结婚,悠悠隔山陂。
思君令人老,轩车来何迟!伤彼蕙兰花,含英扬光辉。
过时而不采,将随秋草萎。君亮执高节,贱妾亦何为!(《冉冉孤生竹》)
这是爱之怨,但温柔得让人无所措手足。我发现,《古诗十九首》中的爱,一点也不浪漫,不刺激;恰恰相反,是那么家常,那么平实。它不是刺激我们的感官使之亢奋,而是抚慰我们的心灵使之安宁;它不是激起我们的热情,而是抚慰我们的创伤。这是一种使人安宁的爱、使人平静的爱,是一种浸透着亲情的爱。我们不是有那么多的“戚戚”与不平衡吗?我们不是有那么多的忧虑与恐惧吗?这爱让我们平静,让我们心平气和,让我们与世无争、逆来顺受,让我们抛别世界的繁华而独守爱巢,并从中找到满足。
这种爱怨,如柳梢之风,吹面不寒;如杏花之雨,沾衣欲湿。就那么缓缓地,一点点深入,一点点浸润,最后深入我们的骨髓,深入我们的心房,让我们骨折心惊!
中国古代诗歌常常是以日常普通生活为基本素材的。诗歌不是对生活以外或生活之上的东西的仰望与想象,也不是一些与众不同的人物的与众不同的生活的反映,一般情况下,也少见一小撮精神贵族孤绝的精神之旅——这样的作品当然有,比如屈原的一些作品,但尚不能改变中国古代诗歌的整体的日常性特征。即便是屈原这样独处时代台阶的最高端、独自成为一国之人的另类的诗人的作品,除却《九歌》《天问》,大多数作品,包括《离骚》,仍是以他自己的生活为素材的。在中国人的观念里,诗歌是生活的伴侣,甚至就是我们的日常生活,它不但不远离我们的生活,事实上,它就是我们生活的一部分,是我们丰富的生活内容之一。比如说,假如我们今天要去赴朋友的约会,在约会时我们会交谈、宴饮、游玩;兴致来了,我们也许还会写诗、吟唱,或者,在活动安排里早就有了这一项。值得注意的是,这写诗吟唱也就是今天诸多活动中的一项而已,它并不特殊,并不高于其他项活动,比如交谈、宴饮。
于是我们就可以这样来解读中国诗歌史:它既是我们的精神史、心灵史,也是我们的生活史;既是我们内心隐私、情感的表达与精神的流露,也是我们日常生活的反映。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我们就能理解中国古代诗歌的一些常见题材了,比如田园题材,山水题材,战争题材,婚恋题材等等,我们必须承认,它们确实是日常社会生活的基本内容。在婚恋题材中,包括了有关女性题材的基本内容。女性在文学中的出现,也大多作为婚恋的对象,且常常是被动的、软弱的,甚至常常是被戕害的、被侮辱的,而这就是生活,是生活的习以为常的恶,是我们熟视无睹的恶。但文学的锐眼与正义也在这里:当社会把她们当作弱者来欺凌的时候,文学则成为她们的喉舌。
在这类题材中,弃妇诗与思妇诗(又可称作闺怨)是最具代表性的两类。弃妇当然是被她的男人所抛弃;而思妇往往又是为她的男人所疏远与轻忽,甚至遗忘,遗忘在一个他不会再回去的角落,而她,就在这个角落等待与思念。是的,当男人因为各种原因或各种理由而离家外出时(常见的当然有兵役、徭役、经商与游宦),独守空房的妻子就成了一个寂寞的思妇,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我们不要小看了这个主题,因为它就是生活之痛,就是人性之痛。旷夫怨女乃是悲惨世界之最常见的世相之一,他们也是苦难人生的人证。正如弃妇往往是人性丑恶的人证,思妇则往往是人生苦难的人证。他们都以小见大地指向一个深远厚重的话题。
在中国传统诗歌中,思妇是极其常见的,每一个时代的诗页上都有她们的泪珠与叹息。这与中国古代的社会情景是相符的。我要特别说明一下,中国古代诗歌中的思妇诗、弃妇诗,其作者往往倒是男人,是一种拟代体的作品。这是否可以看作是男性在对女性集体犯罪之后的良心忏悔,我不敢说。但这一类拟代体的作品确实在揣摩女性的心理与苦痛,我们可以把它们看作是女性的自述。
汉末《古诗十九首》中的《行行重行行》一诗,当是它们中的代表作——可能是她的周围弥漫着那个日落帝国的暮霭,使她的形象比其他时代的思妇有更多的内涵、更多的外延,能更多地调动我们的道德情怀与审美情愫:行行重行行,与君生别离。相去万余里,各在天一涯。道路阻且长,会面安可知!胡马依北风,越鸟巢南枝。相去日已远,衣带日已缓。浮云蔽白日,游子不顾返。思君令人老,岁月忽已晚。弃捐勿复道,努力加餐饭!
在这个以思妇口吻叙述的诗歌里,“她”与她的那个“他”,既有“相去万余里”的空间暌隔,更有“相去日已远”的旷日持久。“她”不仅有深刻的相思之苦,以至于“衣带日已缓”,巧妙地借衣带之宽缓描画出人之憔悴消瘦;且“日已”二字,又写出这是经日累月的消磨与煎熬,如油枯灯干。而且,“她”还有深重的担忧之情——借“浮云蔽白日”的比兴,见出“她”之猜测与忧虑:“他”是否在外面另有所欢,以至于“游子不顾返”?而“她”呢,虽然一边是“相去日已远,衣带日已缓”,独居之时,无奈于时光之迟缓;一边却又惊觉“思君令人老,岁月忽已晚”,揽镜自照,震惊于青春之倏忽。而青春消逝去,容颜老去,又使得未来更显绝望。我们设想一下,一个独守空房却又毫无独立的政治、经济地位,眼巴巴地盼望着丈夫归来的“她”,心思里会有些什么?不外乎对对方的相思之苦,对对方另有所欢的担忧之情,对自己青春流逝的恐惧之心,当然还有努力保养自己以使青春暂驻以待所欢的苦心。这曲曲折折的心事,凄凄婉婉的心情,温温柔柔的心灵,总之,这一份承担太多的苦心,全在这短诗中得到了体现。
人们常用“温柔敦厚”来评价《古诗十九首》的风格,这当然十分正确。但我们要知道,这种风格来自于作品中主人公情感的缠绵与温柔。即如这一首,“她”担忧对方变心,焦虑自己变老,一切都会变,但她自己的温柔不变,对对方的深情不变。这是绝望中的坚持,绝情中的深情,冷酷中的温柔。
《古诗十九首》中的女性,不仅要人爱,而且,她们能爱人,会爱人,她们是男人的故乡。可是,男人们的回乡之路,往往那么漫长,漫长得花落人老。读这一类的诗,我们确实可以体验到传统女性的爱心与苦心,为她们的爱心而感动,为她们的苦心而恻然。她们心柔,心苦。
客从远方来,遗我一端绮。相去万余里,故人心尚尔。文彩双鸳鸯,裁为合欢被。著以长相思,缘以结不解。以胶投漆中,谁能别离此。(《客从远方来》)
远方的“他”给她捎来了并不特别珍贵的一块丝绸,竟让她感动得潸然泪下。被感动了的她越发痴情,并且到了失去现实感的程度:她没有用这丝绸做衣服,而是用它缝制了双人合用的“合欢被”,并以长相之思(丝)缝缀,以不解之结结之!她一边做被子,一边内心暗自发狠:我俩如胶似漆,胶漆融合,谁也分不开我们!感动我们的,就是她所提到的这颗“心”,故人心未变,她的心更痴,人心未死,人心未死啊!我们一下子触到了那遥远时代的心跳,体味到了一千八百多年前的温热……
(节选自鲍鹏山《中国人的心灵》)
微信扫码分享